德里克·沃尔科特黄昏的诉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散文集与加勒比文学深刻审视
摘录丨杨思琪
《黄昏的诉说》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诗人沃尔科特的第一部散文集。精选了他20多年来在《纽约书评》、《新共和》等杂志上发表的多篇重要论文。文章和诺贝尔奖获奖演讲。在这些文章中,沃尔科特评论了海明威、休斯、洛厄尔、布罗茨基、弗罗斯特、拉金等一些现代著名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充分展示了他作为诗人的能力。艺术观念和深刻的观察。
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体现了他对加勒比地区后殖民文学和文化的感人而深刻的审视,呈现了他对诗歌和戏剧创作的总结和反思,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沃尔科特及其迷宫诗歌。重要的价值。沃尔科特的文章和他的诗歌一样,意象复杂,气势磅礴,融合了西方古典与现代、“旧世界”与新世界的诸多文化元素。这本散文集就像是一本集优雅、简洁和辉煌于一轴的集子。沃尔科特在一幅统一的画面中,为他所发展的每一个主题带来了抒情的力量和融合的智慧,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极其重要的诗意声音。
在这本散文集中,沃尔科特为他最喜欢的诗人罗伯特·洛厄尔描绘了一幅生动而个性化的肖像,我们既可以称之为诗歌评论,也可以称之为传记。在这篇高度个人化的评论文章中,沃尔科特写下了他对洛厄尔这个人和他的诗歌的理解,并谈到了他一生中与洛厄尔交往的酸甜苦辣以及他对这段特殊友谊的感受。他珍惜并承认洛厄尔对他的巨大影响。 (“至于诗风与洛厄尔的相似之处,我早已放弃挣扎。”)
在沃尔科特眼里,洛厄尔只是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伟大诗人。当他生病的时候,乌云笼罩,但当云消雾散的时候,他又无比温柔。他的“头又大又方,但它只是一个头”。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首脑,他始终有着平凡的心态,拒绝背负任何光环;无比骄傲又无限谦虚;他能够柔化和模糊周围事物的轮廓,使日常生活变得朦胧;他认为人类政体已经过时。而在他敏锐的探究下,历史不再是一个被审视的对象,而是一种难以理解的重复。
《黄昏的诉说》,【圣卢西亚】德里克·沃尔科特着,刘志刚、马少波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论罗伯特·洛厄尔(摘录)
德里克·沃尔科特

大多数诗人的传记都是不可靠的。它们一出版就成了小说,情节、事件和对话像小说一样来回回响。真正了解一个人,不是笼统地谈论他的生活,而是了解他的一举一动,所以往往很难用言语表达。如果传记的主人公是一位诗人,那么精心炮制的人生经历就会把他的诗变成次要情节,读者只能从叙述的表情中获得快感。这本传记成了扶手椅的延伸,诗人的真实面貌在读者的脑海中被模糊了。
无论诗人的人生经历多么独特,最终都会化作扉页上一系列椭圆形的肖像。如今洛厄尔已成为这样的一幅肖像——他的出生和死亡的岁月已经完成,生命的诗篇已经结束。
我们都是可怜的路人,
被警告给予
照片中的每个图像
有一个活生生的名字。
- “结论”
洛厄尔的生活支离破碎。他六十岁时去世。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精神疾病中康复,并患有长期的恐惧。他早年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我不安”。
(我的想法不对)
。然而,帮助他康复的不仅仅是药物,还有诗歌创作的力量。这种力量侵蚀了他的理智,但也救赎了他。洛厄尔生性英雄,他对诗歌的崇敬是狂野的。尽管精神疾病一直伴随着他,让他辗转于疯人院、收容所和医院之间,但他从未完全失去理智。在临床上,他的躁狂发作被记录为一长串的崩溃和失常,但它们给他的笔增添了一种强有力的、打破束缚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通过诗行来释放。

罗伯特·洛厄尔
如今,那些冷汗已经凝固成光辉的时代,在他光滑的大理石半身像的额头上!我们盯着书封面上的脸,眉毛遮住了眼睛里痛苦的目光。我们终于完成了他的雕像,这是他在世时我们不敢做的事情。想到用死人的语气谈论他,不再叫他洛厄尔,甚至卡尔(卡尔是洛厄尔的昵称,他最亲密的朋友这样称呼他),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熊。他的诗总是在当下熠熠生辉,眼中克制的痛苦依然悲伤。所以我们退缩并寻找其他地方。
在他生前,我们盯着他巨大的脑袋,听着他温柔的笑话,看着他在空中挥舞的双手……一百年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个人一定有着非凡的声誉。现在这个人已经去世了,读他的诗我们更会心颤。洛厄尔坚持写作,他的作品令人惊叹。他的头又大又方,但这只是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头。他始终心态平凡,拒绝背负任何光环;他极其骄傲,又极其谦卑。他可以柔化、模糊周围事物的轮廓,让日常生活变得朦胧和不确定;他认为人类的政治制度已经过时;在他敏锐的探究下,历史不再是一个被审视的对象,而是一种不可理解的重复。
如果说现代人的痛苦已不能再谱写成一出光辉的悲剧,而是以崩溃告终,那么在洛厄尔之前,还没有哪个诗人能如此深刻地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进入中年之后,他的诗常常回避这种接触,因为它像新鲜的伤口一样滴着血。随着时间的推移,伤口会结痂,因为暴露有助于愈合,但来自笔记本
(笔记本)
和“历史”
(历史)
从两本诗集来看,依然是有血有肉的。洛厄尔的创作无不指向创作本身,他的诗歌无不讲述创作诗歌的痛苦。这是体力劳动。他从来没有清理过书房或雕塑室里的杂物来向你展示成品。在《历史》中,你可以看到雕像的骨架、无形的碎片,甚至还能瞥见变形的痕迹和情感的流露。这种做法很容易招致批评,但洛厄尔的每部新作都极具颠覆性,让批评者噤声。他们只能远远地埋伏观望,直到洛厄尔的灵魂再次呻吟,让批评者们沉默。创作能力上存在明显的裂痕。批评洛厄尔的诗歌更像是探测地震,而不是做出审美判断。
洛厄尔学徒期间的写作狂野,年轻时写下的每一行诗都蕴含着强烈的野心,常常为了追求快速的节奏而牺牲韵律。他无法控制诗的缓慢进展,有时甚至让它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在空中疯狂飞翔。即使速度稍微慢一点,读者也能感受到困难。收录于诗集《威利勋爵的城堡》
(厌倦勋爵的城堡)
小说中,无数的对联像呼啸的火车一样从读者的感官中掠过,快得让人无法理解其中的象征意义,只留下令人瞠目结舌的空白。
他引用了克里斯托弗·马洛的话
(克里斯托弗·马洛)
诗歌《时光飞逝》
(时间运行)
,但时间在这里徘徊:
时间过得真快,车窗上星星闪烁。过去的
这是从火车上看到的城市直到最后
它的深色玻璃块变得越来越大,
从哥特式教堂反弹。中在
戒指。我要死了。撞击的石头
像一堆砖头和骨头一样倒下
破碎、粉碎、变成玻璃
在牧师低声做弥撒之前……
——《廊子与祭坛之间》
这些爆炸性的句子不仅仅是噪音。虽然这首诗是在“大爆炸”之后写的,但洛厄尔像任何优秀的年轻诗人一样,淡泊如惜字如金。这就是诗人的本性,但上面这段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没有读到多余的句子,但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过于强烈甚至令人反感的调整策略。诗中的激情看似热烈,实则冰冷,有过激的缺点。每节经文都经过单独打磨,显得毫不费力。有些层次被抹去了,但读者仍能感受到他们强烈的情感。擦除的基础是双关语——“模糊性”的残酷别称。驶过的车窗同时反射着泪水和星光。泪水从玻璃般的瞳孔中流淌出来,就像星光透过车窗一样。诗中的每个字、每行都包含着另一首诗,但诗行的速度和节奏并不匹配。诗的前两行本应表现悠然的回忆,但读者的实际感受却恰恰相反:泪水以五步急速滑落,对联则加快了诗的速度。 《终于》之后的诗句并没有直指内心,成为追忆般的独白,而是意气风发,成为宣言。这首诗的行进速度是从哈特·克莱恩那里借来的
(哈特·克莱恩)
,但连接却像铁链一样清晰可见;在克莱因最精彩的作品中,这种联系是看不见的:

多少晨光,从涟漪的栖息地,
海鸥浑身被冷气包围,用翅膀拍打着、转动着。
(王敖译)
克兰的诗中只有一个动作——海鸥的飞行——整个诗节都围绕它旋转。
洛厄尔的风格截然不同:
我们就像一个大团体
野生蜘蛛抱头哭泣,
但没有眼泪...
——《1961年秋》
这种差异体现在以小写字母开头的随意亲密感(我在诗中放弃大写字母也是受他的影响),在《哈德逊河口》中也有体现
(哈德逊河口)
一首诗中的复杂技巧也涉及火车意象,表现出一种松开领带的自信:
一个人站在观鸟者的位置,
来自被遗弃、耻辱
西屋电气电缆卷筒被铲掉
盐和胡椒斑驳的雪。
通过计算来自三十个状态的字符串
破旧的卡车到了,他无法
发现美国。他们咆哮并摇摆
穿过他脚下的铁路支线。
《威利勋爵的城堡》中有一首早期的诗,诗中火车像时间一样飞驰。在这首后来的诗中,嘎吱作响的马车终于停了下来。
他低下眼帘,
当冰在野外漂流时,
它们沿着哈德逊河漂流到大海,叮当作响,
就像七巧板的空白面一样。
岁月让他变得冷漠,也让他的野心妥协了。这种变化体现在散文词“叮当”上。
(勾选)
上面是冰块的破裂声、炸弹的滴答声、车轮的滚动声和手表指针的转动声,还有海洋附近浮冰即将融化的声音(暗指洛厄尔 1967 年的诗集《靠近海洋》) 。它的前面和后面也都是普通的单词——我的意思是,乍一看似乎很平常,但实际上很精彩。
他对《奥瑞斯提亚》的翻译
(奥瑞斯忒亚)
(现代戏剧诗歌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但长期被批评家忽视)洛厄尔的技巧找到了平静。威廉斯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埃斯库罗斯的风格在他的写作中融为一体。他在纽约公寓对面的墙砖上看到的光并不像雪莱的诗歌那么明亮,也不像叶芝的大理石光泽或华兹华斯难以形容的辉煌。这是纽约本身、现代建筑的光芒。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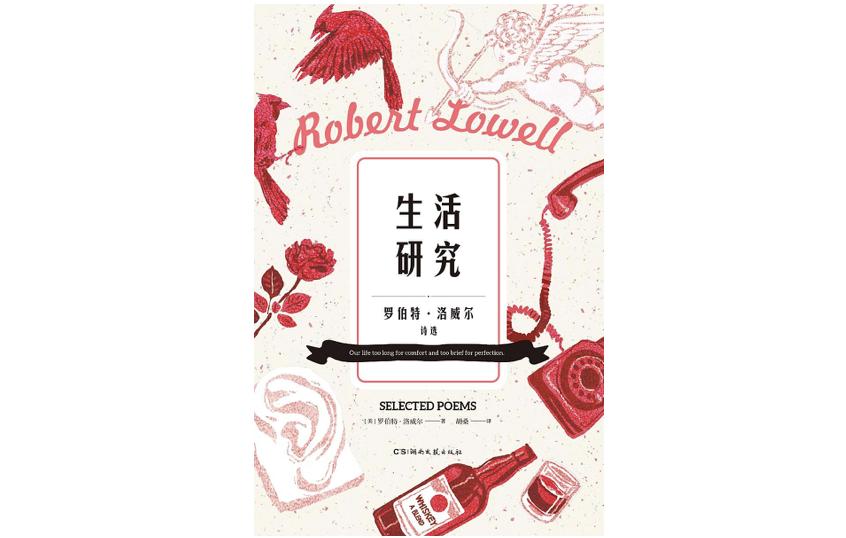
《生命的研究:罗伯特·洛厄尔诗选》,[美]罗伯特·洛厄尔着,胡桑译,普瑞文化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威利勋爵的城堡》收录在本书中。
好的诗人的风格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会在随意的谈话中闪现出来。在私人场合,诗人的感悟纷纷迸发,与他们喝上几杯,比读一篇诗评更有收获。
有一天,我在洛厄尔的公寓,出门前我正在系他的领带,他把我的领带放回了宽松的状态。 “休闲风格,”他说,他的手很大,不像花花公子的手掌。这次修正的非常有技巧,不经意间就显露出了风格。 《靠近海洋》
(靠近海洋)
和“献给联盟死者”。
(致死者联盟)
这两本诗集出版时间相距不远,他那段时期的创作给人一种轻松随意的感觉,就像一个只穿衬衫、把夹克搭在椅背上的天才。他在诗中描述了写作僵硬、节奏麻痹的状态,描述了当众朗诵时,他发现自己的诗句生硬难读,所以就如省略旁白一样跳字。这是他从“垮掉的一代”和威廉姆斯的诗歌中学到的东西。不过,他的自由诗的节奏仍然不是完全“无束缚”的,因为他的出身和他所模仿的前辈大师深深地影响了他。既然“传统的福特车主”(见洛厄尔《威利勋爵的城堡》第33期)可以穿象征暴发户的条纹背心,为什么不能宽松地给自己的写作节奏蒙上一层本源呢?的骄傲。
还有一次(读者请不要以为我对诗人的领带有任何执念),我漫不经心地称赞了洛厄尔胸前的浅橙色和棕色花卉领带,他就把它摘了下来。把它给我。我不会奉承洛厄尔作为诗人,也不会像仆人一样收拾他的衣服。但他对我提出了可怕的指控,好像我就是那种人一样——他对我说:“你知道如何利用人。”那天晚上他正值“爆炸前夕”,夜幕尚未降临,但天色已然暗了下来。黑暗的。我无法像老朋友一样看出端倪。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像赫罗尼莫那样。
(托马斯·基德著名复仇剧《西班牙悲剧》的主人公希罗尼莫以脾气暴躁而闻名)
他再次陷入了狂躁之中。
这种屈辱深深地伤害了我。他是否认为我是想拉近关系并利用这种友谊来推进我的职业生涯?我不是美国诗人,不会考虑这些问题。而且,所谓事业必有传统可循,但我从事的新文学却根本没有传统。与任何新的探索一样,这项事业的成果也在不断更新。我是否曾经像他的寄生虫一样滋养自己?我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他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没有人的想象力比他更广阔。受伤后我问自己,是的,我利用了他,但我利用他的方式与利用古典或现代大师没有什么不同。
在狂热的真理中。
(拉丁语,意思是“隐藏在疯狂中的真相”。)
他重写了荷马的原作:缪斯,为我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他没有使用“愤怒”这个词。我从未亲眼见过洛厄尔生病时有多么乖戾。他那时的出现,会让那些爱他的人充满怜悯和恐惧。但即使卡尔被内心的黑暗所吞噬,他的台词仍然能激发人们的灵感。

我的创作风格一直(现在仍然是)像喜鹊一样——到处戳戳,从一个诗人跳到另一个诗人,但它不是秃鹫。我一生都在练习“模仿收藏”
(仿品)
至于诗风与洛厄尔的相似之处,我早已放弃挣扎。一天下午,安东尼·赫克特和我
(安东尼·赫克特饰演)
, 斯坦利·库尼茨
(斯坦利·J·库尼茨)
、洛厄尔和《诗学》编辑亨利·拉戈
(亨利·拉戈饰演)
聚集在库尼茨位于格林威治村的公寓里读诗。我们原本不去读诗,但卡尔喜欢和朋友聚在一起读诗。拉戈说我写的那首歌《致布鲁克林》“看起来像是一位女性洛厄尔写的”。这个评价有点新意,大概形容保洁女仆更合适。但很少有美国作家掌握了羞辱的艺术。他们本来是想显露自己的聪明才智,结果却说的都是废话。

德里克·沃尔科特
我刚刚讲述了为什么我和洛厄尔关系不好,并且从那时起我就对他怀有很长一段怨恨的故事。当他住院后,我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并告诉全世界,我也厌倦了他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但我记得更清楚的是和解的喜悦。多年后,他邀请我去他位于西 67 街的公寓,这一邀请几乎让我落泪。他打开门,弯下腰,小声地道歉。我给了他一个有力的拥抱,感觉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他的眼神依然紧张,仿佛瞳孔里藏着鬼魂。他把手伸进里面的口袋,我知道他在找什么。他想找到一张他女儿和我儿子的照片。两个孩子年龄相仿,照片是在特立尼达的海滩上拍摄的。
在我和卡尔关系不好之后,我问他的朋友他对别人的态度有多糟糕。但我什么也没要求——什么也没有,要么是暴力的、难以忍受的,要么是可以原谅的记忆。我没有进一步挖掘。他们的恐惧和留下的创伤保护了他。 “怜悯这个怪物,”他写道。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约翰·克莱尔
(约翰·克莱尔)
——他的清醒像恶魔般的云彩一样闪耀,想起埃德加·爱伦·坡跌跌撞撞地穿过巴尔的摩的地狱,想起酗酒的哈特·克莱恩或约翰·贝里曼
(约翰·贝里曼)
但清醒的洛厄尔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恢复得很快,通常不会留下任何疤痕。极度的狂喜也是一种绝望,但哪个传记作家能捕捉到他令人心碎的微笑,他的聪慧、焦虑和羞涩?
这就是让他的传记作者如此困难的原因,他们只能专注于最容易记录的事情,抓住他的躁狂、破坏性事件和痛苦的恢复期。 19世纪的旧诊断标准将诗人视为疯子,有些人认为被诅咒的天才是一个持续的传统(埃德加·爱伦·坡是一种祭酒),因此洛厄尔很方便地被纳入这一传统。但洛厄尔既不是疯子,也不是被诅咒的诗人
(poète maudit,这个概念是法国诗人魏尔伦提出的,指的是极富创新精神却不能被时代理解的诗人)
,他只是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伟大诗人。当他生病的时候,乌云笼罩着他,但当云散雾散的时候,他又无比温柔。他有一种温柔的阳刚之气,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爱。
而那种永无休止的热情,让人想质疑他的诗和诗人本人:你为什么这么逼迫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原谅自己?答案是:因为洛厄尔不说谎。他没有叶芝那样的拜占庭,叶芝的欲望创造了信仰,让黄金打造的人造天堂的愿景成为现实,也没有但丁那样团结一切实体的能力。
(物质)
白玫瑰(《神曲:天堂》第31首歌曲的标题是“白玫瑰”,描述了神圣战士的队伍,以白玫瑰的形状展示)。有一次,我问他对霍普金斯大学的看法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德国号沉船》
(德国号沉船)
你怎么认为?他微笑道:“那些尼姑。”年轻时还写过描写尼姑的诗。他们极其狂热,充满激情,但信仰却消失了。他本可以以更成熟、更温和的方式哀悼信仰的丧失,但他没有天堂——他找不到任何象征来密封这种折磨。叶芝有会唱歌的机械鸟,艾略特有玫瑰,但美国宣和能提供的只是“鸟类百科全书中的条纹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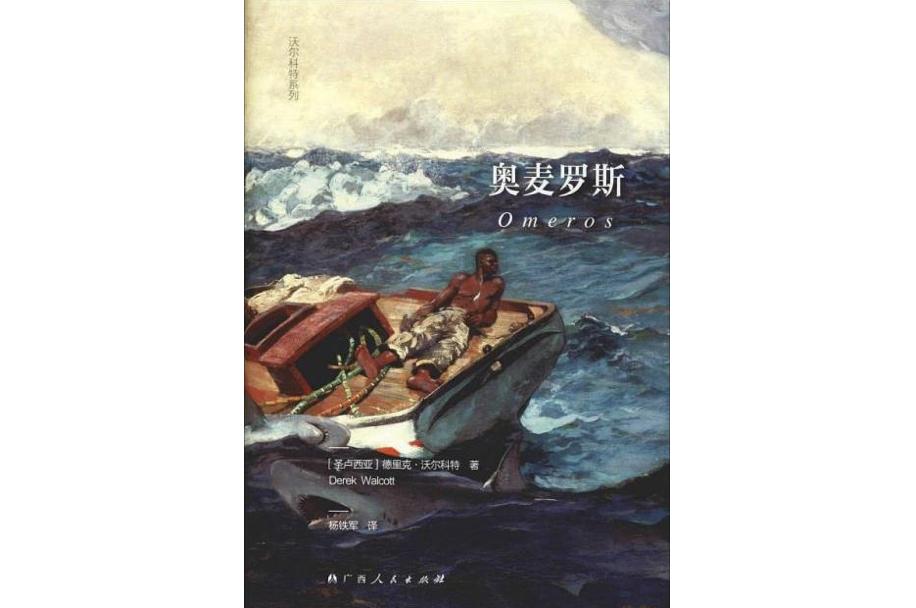
《奥梅罗斯》,【圣卢西亚】德里克·沃尔科特着,杨铁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洛厄尔的诗微微颤抖,时而禁锢又平静,时而流露出家庭生活的幸福。
(英国最早的诗人卡德蒙以其代表作《赞美诗》而闻名,其留下的几个片段构成了英国基督教诗歌的起点)
迄今为止所有的英语诗歌都可以表达。这是一颗智慧的心灵无情地记录着它所遭受的折磨。我想不出还有哪个诗人的文笔能如此温柔和敏感。与之最相似的是梅雷迪思
(乔治·梅雷迪思)
诗集《现代爱情》
(现代爱情)
。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度过一生并不等于走过荒野。”洛厄尔的不肯放手并不是出于对受虐狂的迷恋,而是为了观察诗歌的功效,看看它是否具有治愈的能力;如果诗歌是鹰嘴啄肝,就像维庸一样
(弗朗索瓦·维庸)
或者普罗米修斯发生了什么,然后在洛厄尔,普罗米修斯变成了埃斯库罗斯,受害者是诗的主题,秃鹫变成了同伴。他从不“花时间”当诗人,不像一些美国作家喜欢说除了写作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比如农活、钓鱼。
他的身体像鲸鱼一样无能为力
温暖人心的鲸脂沉入无尽
数英里的海底,呼吸着白色。
刺钩发炎,鱼线拉紧。
——《酒鬼》
“求困于文,善有善报,”他写道。
(本文节选自《黄昏诉说》,广西人民出版社授权出版。)
编辑丨李永波
校对丨翟永军



